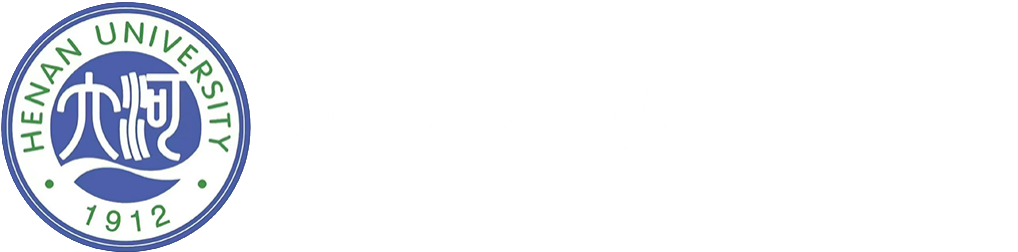为进一步贯彻实施2020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2024年1月24日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于2024年3月1日起施行。《实施条例》的颁布实施,是继《档案法》修订颁布后档案法治进程中又一新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档案工作走向依法治理、走向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推动档案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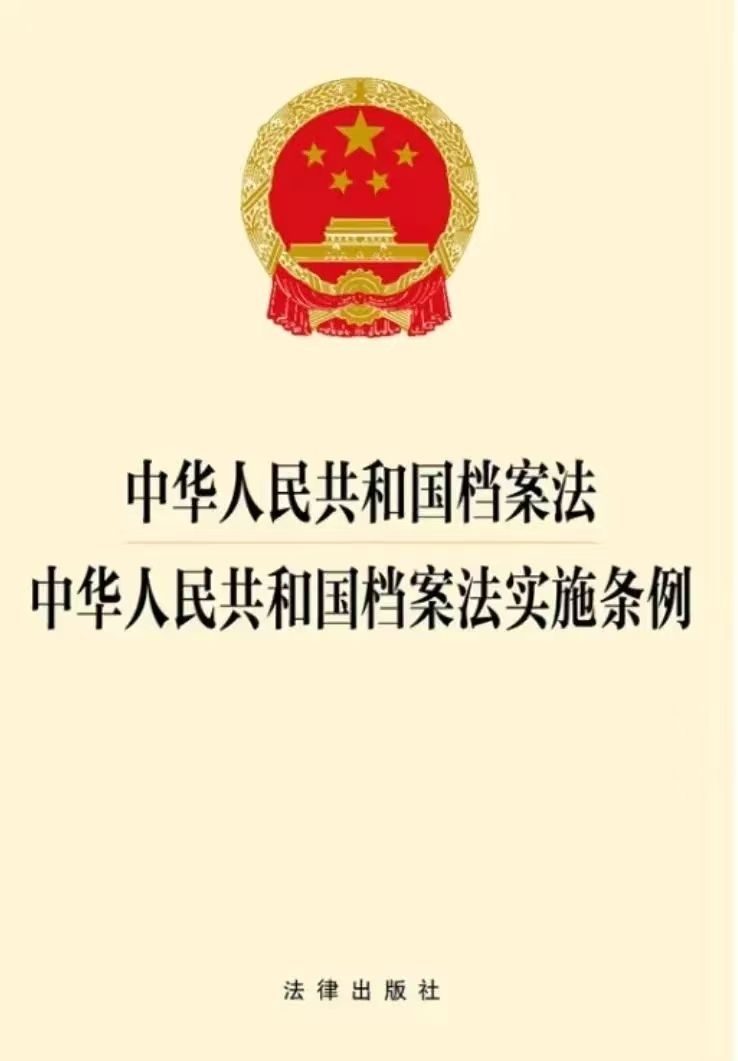
一、《实施条例》的新变化
(一)规范名称变更
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称谓,与其法律属性与法律位阶密切相关,也是其区别于其他规范性文件法律的重要标志。《实施条例》与《中国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都是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都属于行政法规。为防止同效力位阶更高的行政法规相混淆,部门规章不得称“条例”,所以严格意义上讲,“办法”“规定”一般是部门规章的名称,“条例”是行政法规的名称。可见,此次名称修改,既与该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性质与法律位阶相吻合,又有利于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实施,还有利于公众正确判断《档案法实施条例》的效力位阶。另外,更名为“条例”内在地表明,国家档案局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依据《实施条例》制订实施细则或实施办法等部门规章。
(二)内容结构调整
规范性法律文件一般具有相对系统、完整的内容结构,其内容构成与章节排列以及法律要素间关联性,能够直接体现立法技术能力的高低,能够展示一部法的设计思路和价值取向。《实施条例》与《实施办法》相比,其内容构成与章节排列具有明显变化。《实施条例》共8章52条:第一章共7条,即增加2条,原第4条调整至第二章;第二章共7条,即增加了2条;第三章共12条,即删除1条,增加6条;第四章共8条,即增加3条,删除1条,合并原第23、24条;第五章增加8条;第六章增加6条;第七章增加2条,删除2条,吸收原第五章,章内条数没变;第八章附则增加1条,删除1条,吸收原第六章附则,章内条数不变。
(三)立法技术改进
《实施条例》在技术方面的改进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充分尊重上位法的精神与原则。作为综合性法规,《实施条例》与上位法相统一,第1条就明确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规定”而制定。《实施条例》的章节设置和内容构成以新《档案法》的价值导向为遵循,细化与补充上位法内容,相关内容的变动也紧扣《档案法》各项规则制度,增强了不同法律层次间的衔接联系。二是法律文本精细化。作为最具规范性和权威性的法律文本之一的《实施条例》,能准确和充分地表达立法者的意图,符合法律文本的文字使用最基本的要求,继承了先法律渊源的优点,剔除旧法律文本中的非标准立法语言,法条表述严谨明确,语句表述周密,词语使用规范。三是增强了制度的可操作性。为回应新时代档案治理的新任务和新要求,《实施条例》吸纳了《档案法》的执行与实践经验,进一步完善制度细节,坚持依法治档基本方略,积极吸收和巩固档案工作成果与成功经验,明显增强了《档案法》制度设计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二、《实施条例》的突出特点
(一)政治性与规范性的统一
政治性。《实施条例》充分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档案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要求,强调坚持“党管档案”的原则,是档案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最新成果,对实现“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使命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对建设中国特色档案法律制度规范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规范性。《实施条例》通过强制性条款约束相关主体依法行事,从正向约束与反向惩戒两方面实现其规范性。《实施条例》通过明确规定相关主体的法定义务实现正向约束,如第20条有关“应当定期向有关的国家档案馆移交档案”的规定。《实施条例》专章规定“法律责任”,通过明确违法行为的处罚措施以实现违法惩戒。
(二)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继承性。《实施条例》坚持稳中求进,继承现行档案法律法规核心成果,强调与其他档案法律法规的协调一致,遵循“法法衔接”原则,即向上遵循并体现档案法的立法精神与总体要求,又向下汲取相关档案管理的基本准则。合理保留并沿用原《实施办法》有关档案分级制度、档案工作表彰与奖励、相关档案主体职责、档案移交进馆等方面的规定,仅作文字表述上的微调。
创新性。《实施条例》坚持守正创新,在完整涵盖档案工作主要方面的基础上进行了制度与技术创新。如第18条细化和扩充了档案法有关档案工作责任制的规定,首次提出健全单位主要负责人的“第一责任人职责相关制度”;首次提出有关“推进档案查询利用服务线上线下融合”“档案开放利用”工作制度;增设专章规定“档案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档案工作情况定期报送、违法行为调查处理工作;新增专章重点推进“档案信息化建设”,明确规定电子档案管理信息系统、数字档案馆(室)、数字档案资源共享标准建设等方面工作制度。
(三)现实性与前瞻性的统一
现实性。《实施条例》积极回应了档案工作中现存难点、短板,为化解现实困境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为相关主体优化管理措施和技术手段提供方向性指引。第39条明晰了“电子档案来源可靠、程序规范、要素合规”的条件,为电子档案管理提供了科学、规范的法律依据。在确定档案的具体范围方面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区档案工作的现实情况,第2条规定,由省级档案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确定“反映地方文化习俗、民族风貌、历史人物、特色品牌等档案的具体范围”,为档案事业发展预留了自主化与个性化空间。
前瞻性。《实施条例》将先进理念渗透于条文之中,以前瞻视野引领档案事业发展面向未来,明确了档案事业现代化建设的长远目标,为档案工作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如从数据汇集、数据出境、数据共享等方面出发培养数据思维,指引档案工作紧跟大数据时代发展潮流;从鼓励各种社会力量以各种方式参与和支持档案事业发展的角度培养档案治理理念,以实现档案工作协同共治。
三、《实施条例》的价值意义
(一)完善档案工作法律法规体系
《实施条例》作为档案法的主要规范性配套法律文件,在名称上与该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性质与法律位阶相吻合,提高了法律效力位阶,有利于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实施。其吸收和借鉴了档案工作的最新成果,解释和细化了档案法的原则性规定,融合了部分档案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内容,系统优化了档案工作体制机制,在我国档案法规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推进档案治理法治化
《实施条例》从档案机构及其职责、档案管理、档案开放利用、档案信息化建设以及档案监督检查等方面优化了档案立法供给,为档案工作走向依法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条例加大了档案法规制度的供给力度,准确应对档案法贯彻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阻碍、争议,提高了档案立法供给的有效性和及时性,切实保障档案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目标的实现。条例根据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变化,针对档案执法过程中所反映的突出问题,通过优化执法程序,强化执法能力,提升执法效能,明确了档案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和统一性,完善了档案法中的有关规定,增强了档案执法的准确性以及档案权利和档案义务条款的可操作性,细化了档案权利和义务的主体、内容以及档案权利救济途径,提高档案立法供给的有效性和及时性,为档案工作走向依法治理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三)推动档案工作高质量发展
《实施条例》系统优化了档案工作体制机制和责任体系。健全了党领导档案工作的体制机制,细化了各级各类组织机构档案工作职责的规定,明确了立档单位建立档案工作责任制,强化了档案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细化了文件归档、档案接收、档案移交等业务流程。《实施条例》新增“档案信息化建设”专章,及时回应数字中国发展战略,有利于推进档案信息化建设和加快推进档案工作数字化转型。《实施条例》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促进了档案工作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提升档案查询利用服务能力,加大档案共享利用的力度,有助于推进档案治理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