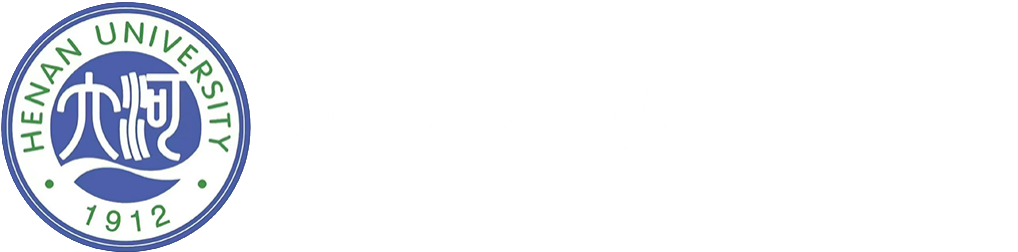河南大学师生在迁徙过程中以及到达苏州后一直面临诸多困难,然而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师生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开展教学科研活动。
(一)迁徙途中的困难与挑战
河南大学当时已经是拥有3000多名师生员工的大学,除了教工、学生、家属等人员,还有图书、设备、实验仪器等教学科研必需品。这么多师生和设备千里搬迁已属不易,况且还要穿越纷飞的火线,仅交通就是个大问题。
因为豫东战役正在进行中,起初出城的师生,基本上都是步行100多千米走到商丘。河南大学在商丘、徐州专门设置了接待站,除了提供茶水等供师生临时歇脚,主要负责安排大家乘坐火车前往南京。很快,在南京浦口火车站、下关码头聚集了一批河南大学的学生。因身无分文,这批学生到南京后遇到了一系列困难,“火车到了浦口,只见滞留在车站的河南大学学生已有二三百名之众,一打听情况,主要是同学们无钱找不到能上的火车,有的同学已经一天多没有吃饭,大家唉声叹气情绪很大”。而且,南京政府担心学生闹事,不允许学生进入南京市,“在下关下船后,见到在下关码头也聚集了一批河南大学学生,他们气愤地告诉我们,南京政府不准南来学生进城,这一下等于‘火上浇油’,我们个个义愤填膺汇集在一起,人多势众硬是闯入南京市,边走边打听,找到了教育部。记得教育部在南京市中心的成贤街。就这样我们进入教育部院内,黑压压一片的学生们势如包围。同学们高喊‘我们要吃饭!我们要上课……’提出要见教育部长”。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田培林接待了河南大学的学生代表,听取学生“要吃饭、要解决到苏州的交通问题、要复课”的诉求,即刻安排学生在附近的饭馆吃饭,饭后派车将学生送到下关火车站,学生分批登上火车去了苏州,对于后来陆续到达的河南大学师生,安排了专人和河南大学一起处理赴苏州事宜。
(二)师生安置面临的挑战
对于突然涌进苏州城的河南大学来说,师生3000多人的吃、住问题如何解决,学校的教学、科研如何开展,安置下来殊非易事,更何况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最为激烈、物价飞涨的年月。“河南大学校长姚从吾氏,于前日由京抵苏,该校校舍,现虽暂假纯一中学及苏州中学两部,惟以开学期近,亟须迁让,故深为焦虑,对三千一百余名员生,就学与宿舍,尚无相当地址,姚校长除晋谒省教育厅长陈石珍,请予设法,并即返苏垣,定明日柬邀此间党政军首长及社会贤达,举行座谈会,请求协助将校址觅定,以安顿苦难之莘莘学子。”由于8月正值暑假期间,尚可暂时借用纯一中学和苏州中学的校舍,但也只是权宜之计。为此,姚从吾校长除拜谒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外,还下了请柬邀请国民党党政军头脑及社会贤达座谈商量解决之道。同时,姚从吾还请云南宿耆李根源出面帮助解决这一问题,李根源给有关人士发来了电报:“苏州河南大学姚校长从吾先生,请转钱慕尹、钱梓楚、单束笙、许宝光、严欣淇、宋铭勋诸先生,暨诸绅老均鉴,河南大学奉命迁苏,三吴文化,发扬光大,实深利赖。昨得姚校长电告,校舍阙如,难以开课,甚盼诸公鼎力协助解决,俾得如期上课,专关作育,专电奉恳,敬请道安,弟李根源叩未柬。”
社会各界人士先后付出的努力大大缓解了河南大学的燃眉之急:“姚校长马训导长对校舍房屋已觅定六处,计有沧浪亭河南会馆(三贤祠)、通和坊湖南会馆、中正路顾家祠堂,及怡园、狮子林贝家祠堂、平江路混堂弄杨家祠堂等六处。但该校原有六院十七学系,及产校、护校、高工、实中等四五附属学校,师生二千六百人左右,所有房屋尚不足容纳,现正继续寻觅中。所有租借房屋,大部为情借,屋主对河南大学流离来苏殊表同情,租金方面格外低廉,校方亦深为感激。……该校购存北平图书一部分及商借钱穆教授私人藏书,现正设法南运,留存上海之国外之书籍,及由教部配购之器材仪器,即将由沪运来。”“该校迁苏同学因感于漫长暑假中,学习中断,自动发起举办学术讲习会,预定每周假苏州中学大礼堂举行。寓苏学者钱穆、顾颉刚、郭绍虞等,将应河南大学之请在文学院任教。”字里行间,苏州人民敞开胸怀欢迎河南大学的坦荡与热情毕现。钱穆不仅给学生授课,而且将私人藏书贡献出来供师生借阅。
1948年10月10日,河南大学在苏州隆重举行开学典礼。校本部即总办公处,包括校长室、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与行政会议,设在怡园。理学院设在怡园后的顾家祠堂,文学院设在沧浪亭三贤祠,法学院设在当时的金城银行仓库,农学院设在西北街104号狮子林后院,工学院设在丁家祠堂,医学院设在现在的公园路体育场,图书馆设在湖南会馆。
(三)后勤与教学保障面临的挑战
与全民族抗战期间异地办学的艰苦性相比,这一次河南大学的处境更加艰难。无论是节节败退、焦头烂额的国民党政府,还是步步推进、不断取得胜利的人民政府,此时均无力顾及河南大学的管理细节,许多事情不得不靠学校自己解决。1948年6月30日,姚从吾校长即拜见吴县县长(时苏州撤市,隶属吴县),商讨解决师生的衣食住行问题。7月底,河南大学训导长马非百、代理总务长杜新吾、教授李承藩三人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依然是请示解决校舍、教具、学生生活、教职员安定、后续来苏师生交通等一系列急迫问题。时间持续一个月,从吴县到教育部,足可见问题解决之艰难。其他问题尚可因陋就简、渡过难关,但解决3000多人每天的口粮成了河南大学前前后后一直需要面对的大问题。刚刚开学稳定下来,10月17日,河南大学向吴县米业公会提交了一份公函:
本校计教职员四五七人,学生二五六六人,工役二六二人及已来苏眷属六六五人,共计三千九百五十人。以每人每月需米二斗三升,计每月共需米九百〇八石五斗,相应造具本校员生工名册壹份,函请查照惠允配给为荷。
显然,吴县米业公会解决这么多人的口粮问题遇到了困难,因为第二天河南大学又提交了一份公函:
贵会本年十月十七日粮总字第三四五号公函,以本校员生工及眷属所需食米无法配给,惟承允另想办法以谋兼顾,并嘱派员接洽等由,准此承蒙帮助,无任感荷。兹派本校职员田觉生、蔡宝田两先生携带本校员生工名册一份前来接洽,相应函请查照惠允洽商为荷。
11月8日,吴县粮食商业同业公会出面,代表河南大学向江苏省农业银行苏州分行借糙米壹佰柒拾叁石壹斗。非常时期,农业银行的粮食应该也很紧缺。12月2日,农业银行即致函吴县粮食商业同业公会,催促河南大学归还所借糙米:
十一月八日由贵会出拟,代河南大学负责人姚从吾先生,向敝行借去糙米壹佰柒拾叁石壹斗。兹派敝行职员姚锦池君前来接洽,请赐予归还,以清手续为荷。此致吴县粮食商业同业公会。
到了1949年2月,形势更加紧张。估计河南大学已经无处可以借来粮食,便向吴县县政府提出求救。2月12日,吴县县政府召开了“措借河南大学员生膳食米紧急会议”,商定“暂由县府及积谷保管委员会在积谷项下拨借糙米二百五十石,并且在一个月内归还”。但是,2月28日,江苏省政府即致电吴县县政府,“征存积谷应妥善保管,不得擅自妄动”。然而,在同一天,吴县县长却致函吴县积谷保管委员会,“河南大学借谷急迫,暂予同意,嗣后非经奉准不得擅拨”。吴县县政府设在苏州市内,他们深知河南大学的情况紧急,为了支援河南大学,居然抗命不遵,把自己压仓底的粮食都拿了出来。
与其他专业相比,医学院更为艰难。据多位校友回忆,当时因医学院没有实验室、有些课无法正常开设,学校就想办法联系东吴大学和博习医院让学生去听课和实习;没有教学器材、没有实验标本,师生就自己动手做。虽然条件简陋,但也保证了教学的正常开展。
在如此动荡、困苦的岁月中,苏州人民不仅慷慨接纳了河南大学,还尽可能从各方面予以最大帮助。河南大学甫抵苏州,7月2日,苏州各界就举行座谈会,筹备慰问河南大学师生。会上商定,慰问河南大学物品款项共5亿元,其中,商会负担2亿元,银钱业公会负担1亿元,工厂联合会负担1亿元,裕社社会事业辅导委员会负担1亿元。7月6日,吴县商会即向河南大学送来慰问金2亿元整。敬善中学从新闻报道上获悉河南大学的艰难状况后,将毕业生的话别聚餐费用拿出来帮助河南大学。凡此种种,足以说明苏州人民的仁心厚爱。短短一年的苏州办学,河南大学与苏州结下了不解情缘,谱就了一段可歌可泣的佳话。
(四)管理层变动带来的挑战
1948年12月,校长姚从吾辞职。早在7月份刚到苏州时姚从吾就提出辞职,“因病恳辞,未获即准,约以开学为期”。估计是国民政府教育部与他约定好了,俟河南大学开学再批准其辞职请求,但是1948年10月10日开学后姚校长依然在为学校奔忙。“鄙人自开封逃出后,患高血压及心脏衰弱病,至十二月终辞职方蒙照准;河南大学校务由教务长代理。因于三十八年正月,改就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随古物疏散来台。嗣因改就台大文学院教授,即未再就任他职。”姚从吾先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1946年11月,河南大学校长田培林就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后,姚从吾被聘为河南大学校长,他“坚辞不获”,后来不得不到开封上任。姚从吾是一个有成就的学者、历史学家,学术研究是他的所爱,从始至终几次辞职充分说明他不愿意担任河南大学校长。客观说,面对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府,在离乱动荡中管理一个3000多人的国立大学,姚从吾苦撑危局,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也获得了师生的称赞。但在两个关键时间节点,作为全校主心骨的校长,没有组织全校力量有效应对危机,而是“弃舰先走”,使得河南大学师生不得不奋起自救、渡过难关。
姚从吾辞职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命教务长郝象吾代理河南大学校务。郝象吾非常清楚当时的艰难和局面的复杂,所以他请在学校声望较高的医学院张静吾教授、文学院马非百教授和自己组成三人小组,共同管理校务。果不其然,三人小组仅仅维持了3个月时间,便于1949年3月集体辞职了。杨泽海时为河南大学教育系四年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学生自治会秘书长,他后来回忆了三人小组辞职前后的经过:“1949年2月学生自治会改选完毕。新当选的学生自治会即刻邀请校方三人领导小组成员及各院的部分领导人员开了一次座谈会。三人小组的领导者都是国内著名学者,我们都很尊重。我们自治会作为学生的群众团体组织,有责任向校领导反映学生的意见和要求,而这些意见不过是建议校方公开学校财政,在学校最困难时期让师生对学校如何维持下去心中有底,稳定学校大局。当时法币贬值,物价飞涨,学生粮源拮据,有些拖家带口的教工生活困难,建议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改善师生生活,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的大事。当时我们年轻,又有‘新官上任三把火’的热情,大概三人小组在公开学校财政方面遇到阻力,为此双方对公开学校财政方面产生意见分歧,结果会议不欢而散。原本是为更好地维持学校,建议改革校政、发扬民主、公开财政,不料第二天三人领导小组在怡园校部贴出《通告》,大意是:‘学生自治会提出的要求我们不能实现,我们也没有能力领导,自即日起我们辞去领导小组职务,离校。’这样的突发事件,使学校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
这里杨泽海的说法是“大概三人小组在公开学校财政方面遇到阻力”,三人小组的通告也说“学生自治会提出的要求我们不能实现”。虽然我们不知道确切原因,但是由此可见对于三人小组来说,的确做不到公开学校的财务信息。可以推断,尽管国民政府教育部命郝象吾代理校务,实际上三人小组还是不能完全掌控学校的局面。据杨泽海回忆,“不论三人小组辞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和学生自治会发生的摩擦便是‘导火线’。……看到三人小组辞职布告后,自治会会长刘士燮和我等自知责任重大。这时国民党教育部已逃到广州,自顾不暇。在苏州的河南大学群龙无首,面临着河南大学存废的重大抉择,也关乎着广大师生的命运问题。是让河南大学解散葬送苏城,还是要发扬河南大学的优良传统,将师生团结起来,当家作主,共谋善策,选贤与能带领大家克服困难,不乱不散保住河南大学基业?在这关键时刻,自治会党小组即刻向党组织汇报,当时地下党指示:河南大学不能在苏州解散,更不能葬送在国民党反动派节节败退、中国人民解放军马上过长江的胜利时刻。选出最可靠的人,维持河南大学”。
事情是学生自治会挑起的,而且得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明确指示,所以,自治会出面联合教授会、职员会、工友会广泛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并发动全校师生员工,采取民主举荐的方式,推举郭喧、方镇中等7人组成了校务维持委员会。关键时候,校务维持委员会起到了重大作用:一是维持河南大学当时的局面,不至于战乱中被拆散;二是保证师生生活正常,直到苏州获得解放。